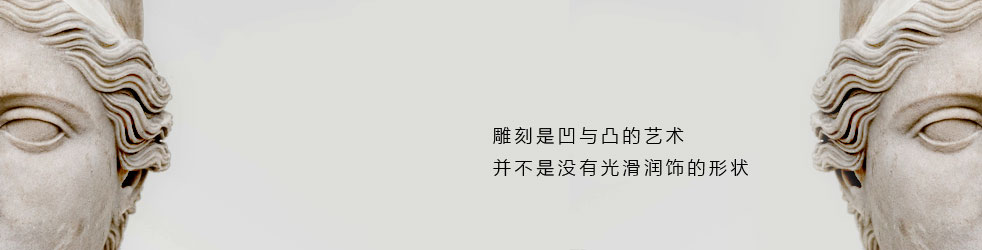
俗到底就齐活儿
——张振福,温开水也能烫死人
我承认我挺以貌取人,长得漂亮的就乐意跟人家多聊会儿→故得证,我和长相、言谈都挺温开水的张振福聊天时一颗心并不那么在焉——直到他现场表演起泥塑。 其实我对什么泥塑剪纸这些艺术一向是不感冒的,一来因为我从小就没什么“乡土情结”,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热衷于表现这么“土”的题材;二来这些东西看起来也的确挺“简陋”。如果把石塑比作正规军,那泥塑就很有些民兵连的味道了。好在我这人耳根子不那么硬,想法变的也快,当我眼看着张振福变戏法似的就做成一件作品时,不由得对这些在自己眼皮底下诞生的小东西有了些兴趣和好感,最终愿意动笔写它一写。 一直在想为什么总是玩剪纸的女人多玩泥巴的男人多,想好久,觉的还是宝玉同学说的是真理——男人都是泥做的!所以让泥做的男人来玩泥,真是太天经地义!而他们对泥土也确实总是有种特别的感情。不论专业与否,他们的成长都是从“泥”开始——小时候玩尿泥,大点玩胶泥,再大点玩橡皮泥,再再大点玩泥丸弹弓,最后要是玩大发了就成了泥塑艺术家,从泥而生自泥而止。张振福正巧就是其中一员。他身上的土坷垃味正和泥塑艺术那满身的土腥味准确地吻合。 在张振福的作品中,绝大部分是表现的豫东农民。他每创作一件作品,总会事先在心里画着模特的样子,凭着脑子里亲切的思绪,刀劈斧砍般一气呵成。这些作品朴实、简练、视觉凝重而又充满了乐观积极、无拘无束的气息,甚至五官都带着股生动的笑意和韧劲,有了种精神上的“工笔”,形式上的“写意”,脱离了手工艺品的匠气,洋溢着剽悍的民间气息。 对于张振福的泥塑艺术,有人说它俗,而且是大俗;有人说它雅,而且是大雅。但无论是说它俗的人,还是说它雅的人,都是用喜爱的眼神或瞧着它或盯着它,一副回味无穷的样子。最近几年,在北京.上海.天津.武汉和郑州等城市的艺术博览会上,张振福的泥塑作品吸引了大批观众住足观看,成为多个艺术博览会上的亮点。与众不同的是,热衷于民间艺术的张振福首先确立了自己的艺术理念,他把自己的艺术定位为“黄土地”系列,也是,那一尊《干杯》,兄弟二人头系羊肚肚毛巾,腰间系根大带赤脚盘腿对坐捧起大碗酒。共同祝福。表现了豫东农民的豪爽.开怀畅饮;那一尊〈〈碾子〉〉年轻的乡村少妇坐在碾子上歇息,怀抱着吃奶的小宝宝,那一尊〈〈今天的收获〉〉,汉子挑起打捞的鱼满载而归。咧开大嘴笑个不停。那一尊〈〈寻找从前的影子〉〉老态龙钟的汉子挽起老伴的手,回忆老两口年轻时相爱的情景。 长期在农村生活,让张振福对脚下的土地有着深刻的了解,对这方土地上的人,有着深切的热爱,也有着深深的敬意,这一切,都最初促使他走上了泥塑艺术的路,他要用泥土的方式去爱他们,用泥土去歌颂他们,如纪录片般如实记录豫东的民风民俗,把生活中最精彩的一瞬表现给大家看。难怪有人说泥土味最足的地方,泥塑艺术家就会多,因为他们更接近底层,更热爱熟悉的土坷垃。这种“爱”,在张振福身上尤其明显。只要不提泥塑,他就一直温温吞吞的,不好烟不嗜酒,说话也犹犹豫豫小声小气,但一旦谁把话题朝“泥”字上一引,奶奶的,大家都死定了!因为张振福可以马上手舞足蹈起来,数不清的词汇从他语里蹦出来,句句不离他心爱的豫东,心爱的泥塑,说要在不断的经验积累和探索中真正形成自己的风格,塑造出属于自己的“土坷垃系列”来。兴起时这个温开水甚至会冒出“我的作品总有一天会成为国宝”这样能烫死人的话来。看来真不能怪他的言行太温了,敢情他把内心的丰富都用在作品的创作上了,然后用让人热血沸腾的作品烫死你。 临道别,张振福说他现在是居士了,也在做一些大佛的泥塑,但他的根基不会离开豫东农村,因为那是他一生的痴迷——瞧人家这青春燃烧的,我都上火了嘴起泡了都赶不上啊!
发表评论
请登录